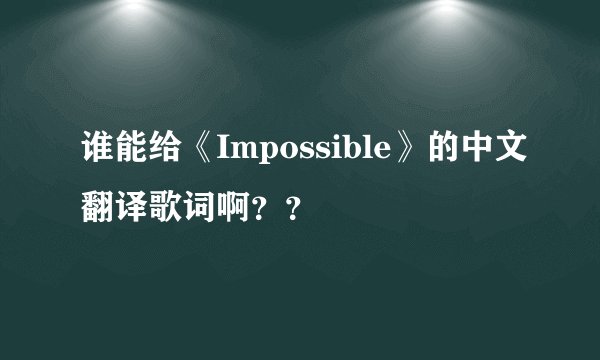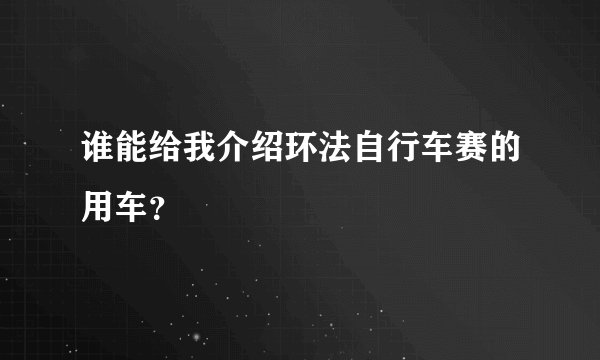金斯堡《嚎叫》 他们撕咬侦探的后颈,在警 车里兴奋地怪叫因为犯下的罪行不过是他们自己进行了狂野的鸡 奸和吸 毒, 他们跪倒在地铁里嚎叫,抖动着性 器挥舞着手稿被拖下屋顶, 他们让神圣的摩托车手挺进自己的后部,还发出快活的大叫, 他们吞舔别人自己也被那些人类的六翼天使和水生抚弄,那是来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爱的摩挲, 他们造爱于清晨于黄昏于玫瑰园于公园和墓地草丛,他们的液体欢畅地撒向任何哪个可以达到高潮的人, 他们在土耳其浴室的隔墙后不停地打嗝试图挤出格格傻笑最后却只有哽咽啜泣,而金发碧眼的裸露天使就扑上前来要一剑刺 穿他们,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爱侣全因那三只古老的命运地鼠,一只是独眼的异性恋美元一只挤出子宫直眨眼另一只径自剪断织布工匠智慧的金钱, 他们狂热而贪婪地交合手握一瓶啤酒一个情人一包香烟一只蜡烛从床上滚下, 又在地板上和客厅里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眼中浮现出最后的阴门昏倒在墙壁上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达到高潮, 他们使一百万颤抖在落日下的姑娘享受甜蜜的时刻, 甜蜜的双眼在清晨布满血丝但仍然准备着领略日出时分的喜悦和谷仓里一闪即逝的屁股以及湖中的裸体, 他们浪荡于科罗拉多在偷来的各种夜车里奸宿娼妓,尼-卡,是这些诗句的主角, 这位丹佛的雄鸡和阿东尼-他的往事令人愉快,他放倒过无数的姑娘在空旷的建筑基地和餐车后部, 在电影院东倒西歪的椅子上,在山顶的洞中,或者在熟悉的幽径撩起憔悴的女侍生的衬裙,尤其在加油站,在厕所还有家乡胡同里的主观论, 他们渐渐消失在巨大的肮脏电影院里,在梦幻中被赶了出来,惊醒在突然出现的曼哈顿, 冷酷的葡萄酒和第三大街铁石之梦的恐怖驱散了他们地窖里的宿醉,既而一头跌进失业救济所的大门, 他们鞋子里渗透鲜血彻夜行走在积雪的船坞等待那条东方河流打开屋门通往一间贮满蒸气热和鸦片的房间, 他们攀上哈德逊河岸绝壁公寓的楼顶在战乱年代水银灯般的蓝色月光下上演惨痛的自杀悲剧而他们的头颅将在冥府冕以桂冠, 他们食用想象的烧羊肉或在包瓦里污浊的沟渠底部消化螃蟹, 他们扶着装满洋葱和劣等音乐的手推车对着街头的浪漫曲哭泣, 他们走投无路地坐着吸进大桥底下的黑暗,然后爬上自己的阁楼建造大钢琴, 他们头戴火冠咳嗽在哈雷姆的六楼,结核的天空被神学的橘园围困, 他们整夜信笔涂鸦念着高深的咒语摇滚为卑怯的早晨留下一纸乱语胡言, 他们蒸煮腐坏的动物肺心脏蹄尾巴罗宋汤和玉蜀黍饼梦想着抽象的植物界, 他们一头钻进肉食卡车寻找一枚鸡蛋, 他们把手表从楼顶扔下算作他们为时间之外的永恒投下一票,从此之后闹钟每日鸣响十年不得安宁, 他们成功不成功三次切开手腕,洗手不干又被迫橇开古玩商店他们在店里自觉苍老暗自悲戚, 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披着天真的法兰绒西服备受煎熬,